風景與權力 | 如何好吃又健康 - 2024年7月

風景與權力
《風景與權力》的目的就是要把“風景”從名詞變為動詞,它的出版曾改變了風景研究的方向。本書收錄了米切爾、薩義德、陶希格等多位學者的文章,包含藝術、人類學、心理學、文學、歷史與現實等許多層面,代表了跨地域、跨學科學術交流的精華成果。文章重點考察風景流通的方式:風景如何成為交換媒介、視覺佔有的地點、身份形成的焦點。每篇文章視角獨到又相互關聯,並彼此深化,反映出人類風景體驗的複雜內涵。
書評
米切爾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的著作精闢有力而令人信服。……[本書]把多位優秀作者的文章彙編到一起,觀點和主題非常豐富,精彩薈萃。——《牛津藝術雜誌》
本文集作者更關心的不是風景作為一種物件或類型如何定義,或把風景視為需要解碼的文本,而是考察風景如何“作為一種文化實踐”。……任何有興趣瞭解對於自然的視覺表現和文化建構的人士都會發現這本書引人入勝。——《加拿大地理學家》
作者簡介
W.J.T. 米切爾(W.J.T. Mitchell),芝加哥大學英國語言與文學系和藝術系的蓋洛德•唐納利傑出服務教授,著有《圖像學》(1986)、《圖畫理論》(1994)和《最後的恐龍書》(1998),是《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雜誌的主編。
再版序言: 空間、地方及風景
致謝
導論
一 帝國的風景
二 "歐洲大沼澤"中的競爭共同體: 身份認同與17世紀荷蘭風景畫
三 系統、秩序及抽象:1795年前後英國風景畫的政治
四 透納與英國的代表
五 “我們的荊編小屋”:湯瑪斯•普林格爾非洲風景中的商業及家庭空間
六 領土攝影
七 風景效果
八 虛構、記憶和地方
九 神聖的風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國荒野
十 荒野現場的圖畫與見證
十一 海灘(幻想一種)
十二 Hic Jacet:這裡躺著……
撰稿人介紹
索引
編輯推薦
本書收錄了米切爾、薩義德、陶希格等多位學者的文章,包含藝術、人類學、心理學、文學、歷史與現實等許多層面,代表了跨地域、跨學科學術交流的精華成果。
文章重點考察風景流通的方式:風景如何成為交換媒介、視覺佔有的地點、身份形成的焦點。每篇文章視角獨到又相互關聯,並彼此深化,反映出人類風景體驗的複雜內涵。
再版序言
空間、地方及風景
W.J.T.米切爾
在《風景與權力》初版幾年後的今天,如果給我機會重新題名,我會出於兩個原因把它稱為《空間、地方及風景》(Space, Place, and Landscape)。第一個原因是,本書已經發表了大量關於權力的觀點,並就此展開了透徹的爭論。如果有人繼續堅持認為權力是風景意義的核心,那麼他將不得不承認,相對於軍隊、政治力量、政府和企業的意義而言,風景的權力是相對較弱的一股力量。風景在人身上施加了一種微妙的力量,引發出廣泛的、可能難以詳述的情感和意義。事實上,無論風景具有怎樣的權力,其效力的不確定性似乎成為一個重要特徵。作為一個形象、形式或者敘述行為出現的背景,風景發揮了環境、場景或視野的被動作用。它常常“被忽視”,而不是“被觀看”,我們也很難說清楚,一個人“正在看風景”這句話到底指的是什麼。
當一個人像我們用日常語調那樣重述那句風景祈使句:“看那片景色”(look at the view)——不是“看那座山”(或那海、天空、平原、森林、城市、河流),而是“看那片景色”,這種獨特的不確定性顯示為一種冗餘。俗語的表達暗示,邀請看風景實際上不是邀請看任何明確的事物,而是忽視所有細節以欣賞一個完全的格式塔(gestalt),一處被某一具體特徵主導,卻不可簡化為這一特徵的遠景或景色。(當這條指令變成“描繪或描述一片風景”時,類似的問題依然可見。)風景祈使句是一種撤退的指令,即從一個位置後退從而抽身而出。正如我們所說,如果一片風景以其誘人的美麗“吸引了我們”,那與這一舉動密切相關的,則是退回到一個更寬廣、更安全的視角,一段審美的距離,以及抵制這片景色可能向我們提出的任何實際的或道德的要求。雷蒙•威廉斯的論斷仍然正確:“一個勞作的鄉村幾乎不是風景。”因此,邀請看一片景色就是建議什麼都不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看觀看本身而已——以便隨著空間在某個特殊地方的展露,對它進行一種意識的感悟。
這促使我想對本書的標題做一個積極的改變。當對風景(landscape)效用的評估涉及到空間(space)和地方(place)時,會發生什麼?這三個術語如何產生共鳴?當然,在許多文本裡,我們把它們互換著使用。一片風景就是一個空間,或是一個地方的景色。在這一話題的現象學和歷史唯物主義傳統中,空間和地方都是關鍵術語,而風景則被想當然地看成是空間和地方的現實特徵的美學框架。在此,大衛•哈威的研究值得仿效。哈威嘗試著把以加斯東•巴什拉和馬丁•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現象的、經驗的傳統和以亨利•列斐伏爾、蜜雪兒•德•塞圖和蜜雪兒•福柯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結合起來。儘管這些傳統中存在許多差異,但它們都同意“空間”和“地方”作為分析的基本範疇的首要地位。相對而言,風景仍然缺少分析。它主要留給對繪畫或造園術感興趣的藝術史家,或是J.B.傑克遜這樣的文化地理學家。就我所知,還沒有人真正嘗試將這三個術語作為一個概念整體來思考。
或許蜜雪兒•德•塞圖提供了最簡單的開始。他依據整整一系列雙重對立劃分出空間(espace)和地方(lieu)之間的“區域”(field)。地方與“穩定性”、“專有的法則”和特定的、有邊界的場所相聯繫。相反,空間:存在於人們考慮方向、速度和時間變數等向量時。這種空間由移動因數的交集構成……與地方相比,它因此沒有一個“專有的”單義性和穩定性。
簡而言之,空間是被實踐的地方。因此,由城市規劃用幾何學所限定的街道通過行人變成了一個空間。同樣,一次閱讀行為也是由一個特殊地方的實踐所產生的空間:一個寫作文本,也就是一個由一套符號構成的地方。
大衛•哈威以一個必須“免受不可控制的空間向量的侵害”(292)的門禁社區為例,回應了這種區分。這種空間向量以貧窮的黑人鄰居入侵的形式存在。事實上,他認為中心城市的主要動力是“地方邊界的穩固性與空間的移動性之間的張力”(296)。在此,我們可以窺見一整套由空間和地方之間的區別推斷出來的為人熟知的對立。德•塞圖將這些術語跟操作與物件、線路與地圖、言語與語言、犯罪與法律、行動與靜止之間的差異聯繫起來。
空間與地方在日常語言中也形成了引人關注的辯證對立。空間具有抽象性和幾何學的內涵,而地方則與特殊性和有質感的密集度產生共鳴。有“外太空”,但“外層地方”聽起來就很奇怪。為某事“騰出地方”(take place)在語法上也與“佔據空間”(take space,或者應該是take up space?)完全不同。place是一個帶有賓語的及物動詞,如:“我把一個罐子放在田納西。”space則僅僅是作為位移和迷失方向之隱喻的謂詞。(一個人能夠通過拉開物體間的距離而把它們“分隔”或“隔開”,因此動詞to space與placing的動作似乎完全相反。)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俗語的內涵顛覆了德•塞圖的對立,因為它們將空間與數位、否定、測量、監視和控制聯繫起來,而地方將有形的、複合的和感官的存與留存在圖繪和描繪的空間符碼之下。一個真空和一塊空地不是一回事。
一塊空地裡充滿了空間,似乎空間是一個地方騰空後便趁虛而入的負空(negative void)。它是“充斥”在一個空殼和一塊林中空地中的幽靈般的空缺。無論怎樣,一個地方基本上和“一個”明確的、有邊界的空間是一回事,而這樣的空間,沒有限定性冠詞修飾,變得抽象和絕對。然而,並不存在絕對的地方,除了博爾赫斯的“阿萊夫”(Aleph)之外,這個神秘的希伯來字母是一個涵蓋了所有其他地方的地方。
與這種二元研究方法不同,亨利•列斐伏爾的經典之作《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基於他所稱的感知的、構想的和生活的空間的區別,堅持一種強硬的三元概念結構。感知的空間大致相當於德•塞圖所說的“空間的實踐”,是“隱匿”了一個社會空間的日常活動和行為,就像同時出現在一塊草皮上的、由人們習慣的行走模式所形成的多條小徑。構想的空間是由工程師、城市規劃師和建築師規劃、管理和意識上建構的領域,正如在(列斐伏爾指出)“數字”和“智力設計的”語言符號中所展示的。最後,生活的空間(列斐伏爾也稱之為“再現的空間”)通過“圖像和符號”傳遞給想像。這塊領域屬於“居住者”和“使用者,還有某些藝術家和……少數描繪並且渴望不止于描繪的作家和哲學家。這是想像試圖改變和佔用的受主導的空間——因而是被動體驗的空間”(39)。
或許顯而易見的是,列斐伏爾的三個範疇大致相當於我一直說的“空間、地方和風景”。然而,我更感興趣的不是加強這種對應關係,而是談論列斐伏爾把整個主題三元化,且抵制二元主義的誘惑這一更綜合的建議。
更具體地說,空間、地方和風景這種表達提供了一個進入我們研究領域的俗語入口,而這個入口,可能三個術語中,單獨一個或雙拼無法提供。因此,我在《風景和權力》再版中要推薦的不僅僅是一些重要的新素材——愛德華•薩義德、喬納森•博爾多、邁克爾•陶希格、羅伯特•伯格•哈里森和我本人的文章——還是一種由對這一更寬廣和分化的理論領域的關注所引起的,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新方法。那麼,人們可以把空間、地方和風景看成是一個辯證的三一體(triad),一個可能從不同角度啟動的概念結構。如果地方是一個特定的場所,空間是一個“被實踐的地方,一個被行動、活動、敘述和符號啟動的地點,而一處風景是那個被視為圖像和“景色”的地點。因此,紐約市的中央公園坐落於地球上一個具體的地方;它是無數活動和實踐的地點;它作為一系列如畫的畫面或從歐洲風景畫衍生出的“風景”而被消費(也被設計為供如此消費)。這些術語中沒有哪一個在邏輯上或先後順序上優於其他術語:一個人可以把空間的活動說成是生產或改造一個地方,或者把一個地方的特性說成使某些空間活動成為可能並且阻礙其他的活動(因此,地方可能被認為具有某種能動作用,儘管德•塞圖的觀點認為空間是一個積極而動態的術語)。風景可被認為是與一個地方首次認知上的相遇,和對它的空間向量的領悟(因此,欣賞風景可能也包括領會——或者無力領會——它的敘述軌跡或符號特徵)。
或許列斐伏爾和德•塞圖的見解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風景中權力的表達是一種法則、禁令、規則、控制的表現——拉康所說的整個“象徵域”。這是列斐伏爾的“概念化的空間”,是由景觀設計師或工程師創作的、被管理或被設計的空間,是巫師宣佈禁止進入的禁地或神聖空間,或者是被殖民官員命名、聲稱擁有並控制的被征服的領土。對於這種把空間看成是象徵域的維度(如同法律或否定)的觀點,我還想補充一個看法,即把地方看成是拉康式現實域的場所,是創傷和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我們說,“這是這件事發生的地方”,但若說“這是這件事發生的空間(或風景)”則似乎有一點奇怪。紀念館或紀念碑被建起以標記一個地方。空間的實踐(儀式、朝聖、遊覽)則可能啟動這個地方,而這個地方則可能變成想像力渲染的物件(明信片、描繪、聲光表演、幻想、記憶)。
然而,我的觀點並不是要嚴格地將空間、地方和風景與拉康的象徵域、現實域和想像域對應起來,而是要啟動這個概念三一體的辯證資源。我的目標是要釋放出體現在這些術語中的理論的白話資源,像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傾聽我們的元語言”。我們需要這樣做,因為我們簡直不知道如何命名這些術語所包含的“領域”或“主題”。我們談論的是文化地理學或人文主義地理學麼?是造園術、環境研究或深層生態學麼?是藝術、文學或者媒體的歷史麼?是地點、區域和領土的社會學、人類學或現象學麼?任何想要圍繞三個術語中的一個來奠定這一探索的嘗試,例如,把“空間”設為基礎概念而把其他兩個看成衍生出的變體,都容易使這個討論具體化並且枯竭。在我看來,最好一開始就把這個主題三分化。這一姿態實際上可能是認知性繪圖中某些基本過程的反射,是在任何感知的或概念的領域確定方向的方法。於是,我們的“主題 ”(實際上理解為地方)要求把空間/地方/風景設想為一個統一的問題和一個辨證的過程。
本版中新編入的文章都從不同的方面引發了這個三一體。愛德華•薩義德的《虛構、記憶和地方》為1998年一次難忘的關於“巴勒斯坦的風景方面”的會議定下基調,展示了媒介(寫作、記憶、想像)如何產生出一個“人類空間”,也就是一個空間 /地方 /風景的複合體,有著具體的位置和歷史,空間向量和運動在其面孔上留下並探查到了傷痕。我自己的關於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國西部“神聖的風景”的文章(為同一次會議所寫),同樣關注一處想像的風景如何被編織到現實地方(例如,美國西部的沙漠、約旦河西岸的沙漠地區)和象徵性空間(如受到法律和軍事權威管制的領域)的結構中。這兩篇文章首次發表的具體地點是約旦河西岸的比爾澤特大學,也是其價值的一個重要方面。兩篇文章又具有雙重定位的意義,在美國背景下如此深深地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產生了象徵的、想像的、現實的聯繫。
喬納森•博爾多關於荒野的文章同樣是一個有著破壞性空間實踐的真實歷史和象徵性控制體制的特定地點,介入了北美和加拿大人對“未被踏入的”或“處女”風景的想像。邁克爾•陶希格關於“沙灘(幻想一種)”的沉思,正如標題所示,是一次對那些想像的海灘的探險,在那裡我們追溯了在“鹽海”中“人類的起源”,也探討了20世紀中作為公共空間的“港口”所受到的現實毀壞,以及澳大利亞悉尼邦代衝浪海灘之類的具體地方的象徵性共鳴。
最後,羅伯特•伯格•哈里森的“Hic Jacet”重新思考了海德格爾的問題,即地方同時被決定並決定了我們“在世存在”,此在。是我們創造了地方,還是地方創造了我們?這個問題的價態變化,把能動性歸於生存的人類主體,或者他們埋葬的地方,似乎使整個空間、地方和風景的問題回到“地面”。無論風景具有什麼樣的權力,無論它向空間和地方展現了什麼樣的權力,它無疑是我們生活、活動、實現自身之存在的媒介,是我們最終註定返回的媒介。
 因為山在那里
因為山在那里 青田街七巷六號
青田街七巷六號 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
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 稻米達人大挑戰:稻田生態及稻米知識問答集
稻米達人大挑戰:稻田生態及稻米知識問答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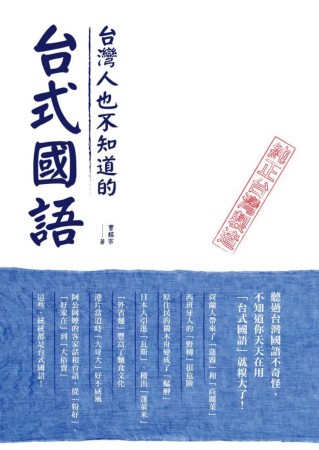 台灣人也不知道的台式國語
台灣人也不知道的台式國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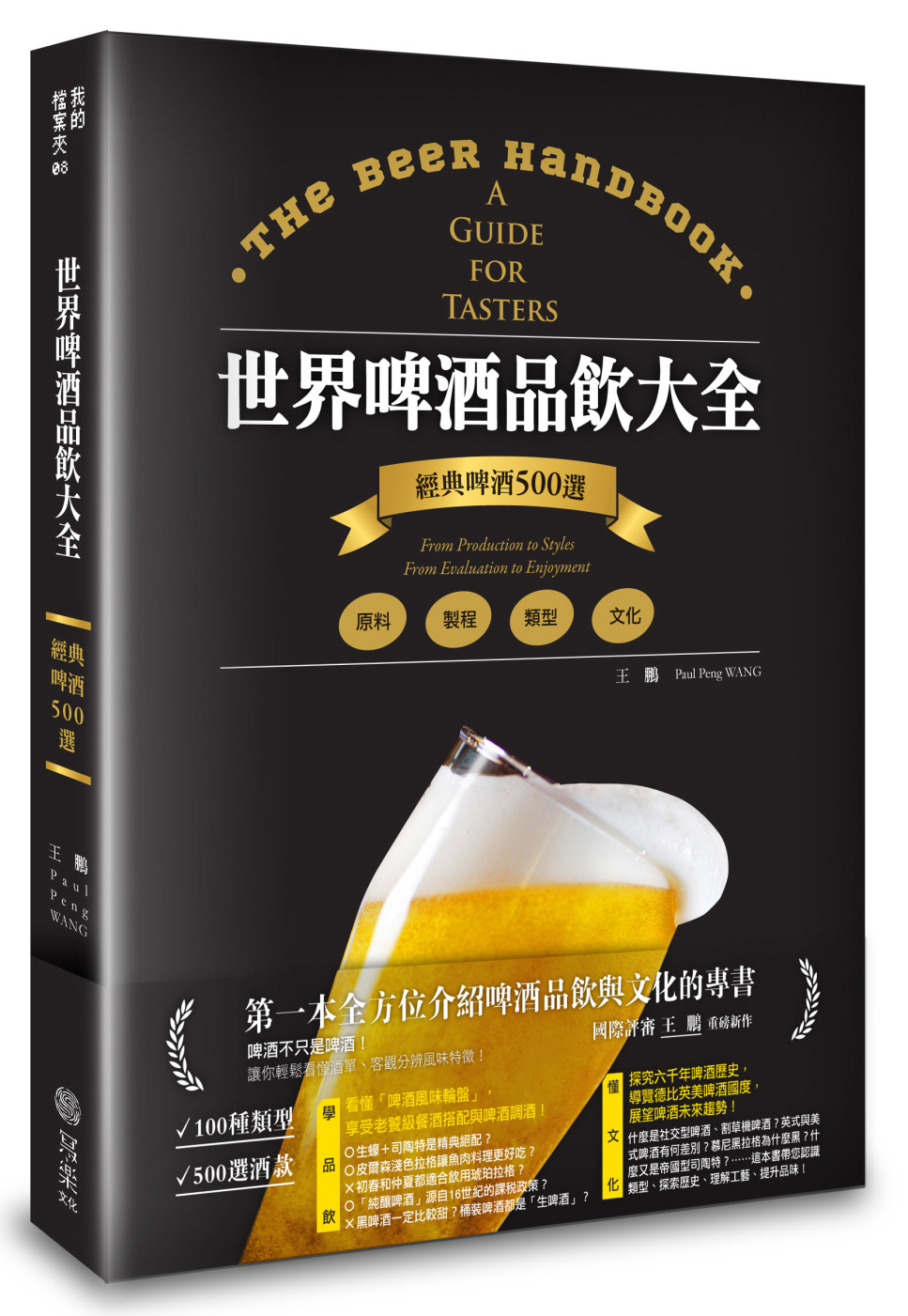 世界啤酒品飲大全:原料‧製程‧文化...
世界啤酒品飲大全:原料‧製程‧文化... 傳統產業大觀(2冊套書):一看就懂...
傳統產業大觀(2冊套書):一看就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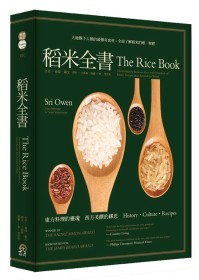 稻米全書
稻米全書